2019-01-14 15:45:01 来源:中国新闻网
“我麻木不仁地摇头,有点矫情地说:最后一次,再为我做一只陶罢。我感到我的内心很荒唐地触动了两个凹凸不平的烙字:爱情。”——《陶之陨》
18年前,高中生张悦然写下这篇文章,主题是早恋。当时,捧红韩寒、郭敬明等人的“新概念作文大赛”风头正劲,她凭借此文获得2001年该比赛的一等奖。

张悦然 摄影师:王旭冬
仿佛一夜成名,她变为年轻人眼中的成功范本。之后,写小说、办杂志,教书,将人生图景不断向前拓展。区别于“新概念作文大赛”举办之初的繁华,她也感受到了当下文学的寂寞,并努力想改变这一切。
作文大赛带来的“成功榜样”
如今,在一些对谈场合,张悦然偏爱深色着装,有时会带一个帆布包。发言时语速不快,声音很平和,“成熟稳重”是很多人对她的第一印象。与当年青涩的样子截然不同。
大约20年前,《萌芽》杂志发起“新概念作文大赛”,在高中生里发掘了一批颇有文学才华的年轻人。张悦然作为第三届比赛一等奖得主,很快被推到台前,接受读者崇拜的目光。
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“新概念作文大赛”有些生疏,对80后乃至更年长的读者而言,它却代表了一种文学潮流,影响力绝不亚于现在最火爆的选秀节目。
张悦然被安排着去各处书店签售,宣传横幅上多半会加上“美女作家”一类的称呼。她每次看到,都会觉得有些局促不安,总觉得那不是自己。
参赛时,她正在山东省实验中学念高中,获奖后得到一个保送清华大学的机会。虽然最终没去成,但并没妨碍经常被作为成功案例提及。
像是感受到作为公众人物的压力,她从2004年开始,两年时间内接连出版长篇小说《樱桃之远》和《誓鸟》、短篇小说集《十爱》等作品,拥有了稳定的读者群。
有人认为,张悦然能够火起来是赶上了文学的繁盛时代:毕竟那时还有那么多人真心实意热爱着写作。

张悦然 摄影师:曹有涛
“很难得,文学曾拥有那么高的地位,获得那么高的关注度。”张悦然喜欢那时的写作氛围,但觉得作为80后,赶上的只是繁盛期的一个尾巴。
“能沐浴到文学的夕阳也挺好。”张悦然声音里带着些许怀念,“毕竟是一个人生舞台,让你能够展示自己”。
编杂志,为文学组个“朋友圈”
获奖几年后,26岁的张悦然萌生了一个想法:编杂志。起因之一,是想念在网络论坛上热烈谈论文学的日子,想给文学一个相对纯粹的交流空间。
于是,2008年,《鲤》出现了,张悦然任主编。
最初,杂志社拥有一个两层的工作室,坐标望京,很多志愿者穿梭往来,跟编辑们争论文学的种种话题。
《鲤》的周围聚集着周嘉宁等作家,像是为文学组了一个“朋友圈”。杂志属于主题书,不定期出版。同时,也会对国外年轻作家的作品进行译介。
张悦然常常被读者们的反馈感动:有人寄来很多照片,拍摄《鲤》的封面,从第一期到最新一期。那段日子她过得相当开心,“那是和文学在一起啊”。
可一段时间以后,《鲤》不得不借助“裁员”的方式存在下去,直到常驻人员只有3个。张悦然自嘲“八成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规模更小的杂志了”。

张悦然。理想国 供图
“我们确实养不起那么多人。”她觉得《鲤》能“活”到现在,秘诀就是人少、规模小,“不用太关注文学之外的事情。创作更好的内容是我一直信奉的理念”。
张悦然把现在的《鲤》形容为“化石”般的存在,必须得努力坚持,“想给热爱文学的人一个平台,要是还能影响到一些人的青春,就更好了吧”。
一个大学老师的理想
如果不算杂志主编这个小小的头衔,张悦然应该是个自由职业者,从大学毕业后就专职写作。这两年,常有新书出版。
2012年,张悦然得到了另一个称呼:老师。那一年,她受聘于中国人民大学,成为写作班的讲师,这是她获得的第一份正式工作。自此,教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
她在教师、杂志主编、作家三个身份中切换,很快把课堂变成宣讲文学的地方:跟学生讨论小说,凭借自己阅读和写作的经验给出视角独特的分析,努力想把文学带进一个纯粹的场域。
“我想把好作品传递给年轻人,希望他们成为长久的读者。”张悦然热切的期待,大学生距离社会生活较远,对文学拥有最真诚原始的渴望,哪怕只是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种子。
也许文学落寞 但可以做点什么去改变
可像很多人感受的那样,“纯文学”处境日渐落寞,爽文、爽剧当道,很多人不再偏向选择看小说。昔日大作家的新书销量不佳,并不稀奇。

作家张悦然 摄影师:曹有涛
张悦然没把罪名全部堆到火爆的短视频上,“就算没它们,也会有很多比文学更有意思、更好玩的东西分散精力,手机阅读改变了获得信息的方式,很多东西都可以打败文学”。
她愿意实际做点什么改变这一切。所以,发起了“匿名作家”计划,还请来24位作家、批评家和文化人,预言他们眼中文学的未来。
整理完大家的预言后,张悦然发现收回的问卷有点消极,“甚至对文学有着一定摧毁性,比如很多作家都预言到诺贝尔文学奖将会消失”。
她自己的看法也不怎么乐观,在一场青年文学论坛上还提出了3个预测,认为将来人工智能可以写出人类最细微的感情,将穷尽人的书写,于是人类写作者只好开始写动物。
“我们都以为文学特殊,唯有它能构建人性复杂的多面性。”张悦然说上述设想很极端,却不全是危言耸听,“如果人工智能可以写尽人性的幽微,那时候作家还能干什么?可能只能写动物吧”。
文学会衰亡吗?她又给出了否定答案。这有些矛盾,可她觉得,作家永远是在唱衰的,但在唱衰里面也包含着期待,包含着他们想要看到的新的可能性。
说他们“背叛文学”太不宽容
就在张悦然作出上述努力的同时,“新概念作文大赛”也已走过20年。在这段时间内,很多当年的参赛者、获奖者,离开了写作或与它相关的领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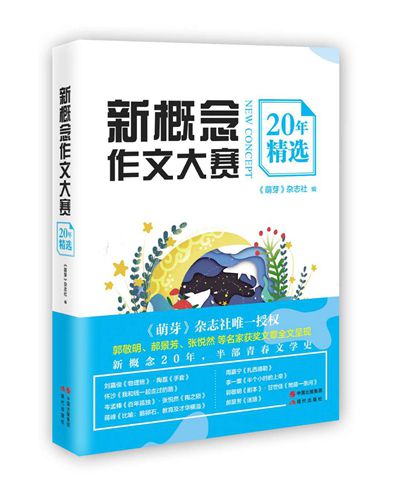
《新概念作文大赛20年精选》。现代出版社出版
有的学医、有的进入金融领域……还有的干脆自己开了个店。他们变成了医生、白领,或者店主。当年名声最响亮的韩寒、郭敬明,除作家之外,也多了其他头衔。
有人开始揶揄:以前想靠着文学成名,如今却背叛了文学。
张悦然还在安安静静写小说,而且越写越像大众眼中“纯文学”的路子。她很少主动谈起“新概念作文大赛”,但又总会被问到一个问题:那些离开的人怎样了?
“不能苛责改行的人吧,说他们背叛文学有点儿太不宽容。”张悦然自有判断标准,“毕竟获奖时只是一群十八九岁的孩子,很难确定稍稍显露的才华,能否支撑他们坚定地把写作当成职业”。
就连张悦然本人,拿到一等奖后,大学选择的也是计算机专业,跟文学没多大关系。直到连续发表了几篇作品都受到欢迎,才决定专心写作。
文学不是宗教,不存在背叛。在她的心里,即便改行后,工作与文学再无交集,可与文学在一起的美好时光不会与人生割裂,“所有离开文学的人,依然会得到文学的祝福”。
偶尔,张悦然会感叹,现在身边还在写作的同龄人,早已不是十几年前那些人,“有对生活压力的考虑,可能也有对文学渐趋边缘化的失望,所以,就离开了”。
那么,她也会走吗?
“文学和每个人都有联系,我心里还是有一种责任感。编杂志,当老师,能把有价值的作家和作品介绍给年轻人,也挺好吧?”张悦然轻快地笑着,仿佛心里早已得出答案。